һ
ʮ�������꣬���߳��¶�ͯ�꣬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ꡣ����1976�꣬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ȥ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ӵ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ź�ɴ�������۾����ܿ��������ߣ����Ӷ�һ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ֵĴ��ֱ������͡�������Щ���ֱ������˵ڶ��������ӣ������Ǵ�ǹ�ĵ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ĸɲ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Ů�ģ���֣��С��ס���Ҽҡ�
���ã���ĸ������ס���ļ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ʯ�꣬��ʯ������䣬�����ļ¡�ʪ�ȵ�7�³�������¶������ίԱ��Ҳ���ˣ���һ�Σ��ҷ�����֣��С����Ҳ�����˺�ɴ��
��������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ѣ��ض�ɽҡ��ĸ��˵��������Ҫ���˰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һ�Բ�������֣��С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ɫ���š���Щ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Լ������IJ�������ſ��ᣬ�����Ǵ�ġ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Ʋ��ܲ��ʣ����˺������ơ�
9��9�����磬�����ӽ���֪ͨ������Աֹͣ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Ҫ�㲥��������ʱ������С����һ����̫����Щ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ڿ��С����ߵ�����ͻȻ�Գ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ǡ�����Ĵ����ȿ�ʼ�Ű��֣����˺��Ӷ��ֵ�һ����ɴ�����ڸ첲�ϡ��������Ķ�ĸ��˵�������˼����ˣ��ܺú����ǵ���ͣ���Ҫ��˵������
��Ȼ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ſ�ʼ���Ÿ��棬ȫ���˶���ɥ��������һ�ţ�����һ����ͥ�������õĻ�С��͵�Ż�Ц֮�⡣
�ڶ��죬ѧУ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ã���ʦ������һ����ƻ�������Ҵ���ȫ��ͬѧ���ԡ����Ե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ˣ�ӡ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Ǹ���ƻ��������
��̫�����䣬���dz��˱�ʹ����Ҫ�ǿ־壬��Ҷ���֪�����Ժ�����ӻ���ô����ȥ��
ס�ںӵ��ϵġ������ӡ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·��Ѿ����˼�ʮ���ˣ��ܲ�����һ���˶�����ȥ���ɡ�û�¶����óԳԣ���˯˯��
�������ӡ��Ļ������ľ�������ȴ�ܿ�Ӧ�顣����һ���£������ֻ���ϲ�ؿ���ᣬ����Сѧ��Ҳ���Ŷ�������ȥ���У���ף������ץ�������š�
��ף��Ὺ��û���죬����̨�ġ�Ӣ�����䡱�������Ļ��������ʤ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ڶ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Ҳ��Ȼ�����ˡ�
������ף��������˳��У�ѧУ��ʼץѧϰ����һ��ȫ�꼶ͨ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ǰé�������һ֧�ֱʺ������ʼDZ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IJ����ϣ���ĸ�ܸ��ˣ���Ҳ���Ժ���
��㺬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ң��ĵܣ���Ҫ�úö��飬���ϸ��У�
�������ʱ�������п���Ӹɲ��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Ӷ�����Ȩ������ܿ���һҲû���ɸ��У������Ҳһ����
���и�ͬѧ�С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IJ����ǿ顰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Ҷ�ʱ�������յ�˵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̫���ˣ�ʮ���˲���һ�������ǻ������˰ɡ���
��ʵ���Ǹ��ܴ�����ѧ����һ�ʷ�����д��Ư�����ˡ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Ǵ�Ψһ�����ൺ��У�ģ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ൺ��Ӫ��ó��˾�ĸɲ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ȻҪ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С���ʱ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룬ʮ����һ����ʲô�ѵģ�
��ʦ˵����־�����Զ��������ҿ�����ƽ�ȶ��У�����᭶��顣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Ŭ�������ż״��һ������ѧ��ľ��������ͨ���ж�û��ȡ�����ǵ������Ӵ˷ֲ档
���ǰ�����ɼ��������ͬѧ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˸��У��������е�Ҳû�п��ϴ�ѧ������Ϊ�и���ѧ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ͨ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ʦת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У���е�������ͨ����ѧ�õ���ѧ��ƾ�����ոı���ũ�����ݡ�
�ҳ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е�־����Ŭ�����꣬������Ӧ��û�����⣬����ȴ��һ��֮���Զ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ʳ��ũ��
��
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½��ġ����ѡ���һ���ļ���һ������ÿ�������ɫ�ij��ۣ���һ������ɫ����ձñ��һֻ�����ۣ���һֻϹ�ˣ����ϻ�����һ������ĵ��ۡ�������һ�ѻ���ɽ����ӣ�����ȥ���ϰ�ʮ�ˣ���˭Ҳ��֪��������ʵ���䡣������һ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һֻ����˯������ɫè����ֻ�µ���«������ס�ڴ���ӵ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ϴ��һ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Ǹ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IJ���®��
��˵�����Dz�����ӵ��ǧĶ����и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˵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ɶ�ã�����ȡ�����̡�
�����ڸ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ʱ���ڵ����ϼ������ģ��������Ϲ���һ������һ���ȵ��ϻ��۾��������۾���ϸ��������һ�������һ����צ�Ƶ���ָ�����ҵĶ�ͷ��˵������ҵ��Ĺ��ӣ�ü�ۣ���ͣ��ر��DZ�ͦ�ı��ӣ��е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ӡ�
����Ҳ���Ǹ����꣬�����ҸϽ����ߣ����߱�˵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ǻ��ˡ��IJ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ҵģ�
�ؼ���ĸ�ף���ӵ��ϵ�һ������ͷ˵�Ҹ���ү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ô����û������ү��
ĸ��ͣ������Ļ�ƣ���Ȧ���ˡ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ȥ��
����ס�ں�֣��IJ����ϵ�С������Ҳ��ǵ��Dz����ʹ������ˣ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֪����ĸ��С��ʱ����ү��ȥ���ˡ����Ǹ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ү�μ���һ֧�����λ��ӣ��ں����ֱ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ˡ��ӻؼҺ����˰���¾����ˡ�Ʋ����һ����ʮ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Ӻ��������ӡ����ѳ�˵������ү����ʱ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꣬��������꣬��С�˻����һ�����̡�
������ҵļ�ͥ���磬һֱӰ�쵽�ҡ��μӹ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й�һ��������飬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顣ĸ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ң��������û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û�˵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Ҳȱ��������
ĸ�Ļ��������᳤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ѵ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д��
��
�������һ���ϱ���ĺ�������Ҫ����ƽ�ȵ���һ�Σ����˸��䣬������ֱ�DZ�Ϊ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ɳ���壬�ָֻ����ϱ��ƺ����£�ע�뽺���塣
��ζ�������ĺ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˳�Ϊɳ���ӡ��ܶ���ǰ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Ͱ���ʯ�ţ���ɳ���š�����Ѵ�ڣ���ˮ���ۣ�ʯ�ű���û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ˣ�����ˮ���ӡ�
�������ӡ��ںӵ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ʱ��ͻȻָ��Сʯ�����ң���֪��������˾����
��ҡͷ��һʱû��Ӧ������
����˵���Ͻ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º��г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һƥ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֧����ǹ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ʮ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ſ���ǹ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ʹ�����С���Ϲ��ӡ����ൺ���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簡��
��ͻȻ��������˵����˾��Ĵ�����¡�������Ц������֪��������˾�˫�ִ�ǹ��˭���Ų������棬������˦�־���һǹ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ء�
������Ц�ˣ�����Ϲ��ġ���˾����书���ܺȾ�����ġ��������Ҳ����ġ���˵ֻ�������Դ�ǹȥ��ë��ϯ��
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ϲ���˵����˾��Ĵ��棺��˾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ݺὺ��ʮ���꣬�Ž��������Ԫ�����质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24��˾�����һ����ȫ���ˡ��Ա�ԭ����ᰡ���Ͻ�����ί�ε��ݱ�12ʦ�н�ʦ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ü����̾ὺ��ʮ���꣬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ˡ��Դ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ͷ�����¡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ͷ������٣��������վ��н��и��ָߵ��������ձ�ί���˸���У�ų���Ҳ�ڽ��ر���§�ݴ����ӣ����ˡ�����ϵ�ʱ���ϼ�������һ���¡��������˰��죬������ϸ�������ҫ�䡣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ͣ�ȴ�ǵ��ϼ������ˡ������ϼ���˭��ս����ԣ��������Ұս��˾�����
������ü��ɫ�裬˵�����ս�ۣ���ĭ��ɣ���ԣ�ָ���14���ˣ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Χ�ż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Լ�����ʮ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ڰ�·�ϴ�Ԯ��һ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Ȫ���ư�躣�˭֪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Ӽ�ѽ������ʹ����˼��ϣ��ŵ�����Ȫ�ư�躸Ͻ����˻�ȥ����ս����ԣʮ�����˴���һ����硣��˾��һ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ȥ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ս�ۣ��ɽ�ս�ۣ�������ս��ͳͳû���ķݡ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ѽ�������˲�ȥҽԺ�������ϱ��ӵ����˸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ָͷ���ӵ��۳������˿�Ĩ�ϵع��ͣ�û������ˡ�
��ʵ�����ί�п���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˺ü����ݶӣ������ھ���һ�ߣ�������ʦ�����Ĵ���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ൺ����·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ڳ��ʲ������һ����
�����ڹ��һ��������һ��ѵ���¾����Ѽ�֧�������ӡ��ط���װ��ѵ�������齨�ɵ�32��������֧���ӣ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ൺ��
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ʷר�ң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ѽ���û�μӻ������ɽ�ս�۵�������
��
վ�ڴ������ͷ���ҵ���ǰ�������ֳ�����һ�����棺
һ֧�����н���ʢ����ơ�ƻ���ԭҰ�ϣ��峿�ķ������ɢ���ŵ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һֱ���쵽��ʡ�ɳ�����Զ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ʿ���ǵ���ǰ�������ʣ���ʧ�����ɫ��Ũ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ĵ̰��ϣ�Ұ���ͷס���չ���һ�ֲ��£���ϡ�м�����͵��¹⣬�����Ƶ�϶�����佫������һ������죬�ڳ�����ӭ��������չ��Ѫս֮���ɳ���ϣ�ս���ݺᣬ���м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ʬ�壬�������˵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Ѫ��ζ�������εΣ������賿�����⡣
ɳ�����ϵ�Сʯ���ѱ�ը�ɼ��Σ��������˵����ں�ˮ�սʿ�Dz��ò����ɹ��ӡ�����ӳ�ں����ϣ��������ԣ�ˮ����ֻ�Գ�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ǧ����ƥ��������̤̤��������ˮ�����ӵ��W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أ��������У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
����1949�����£��й������ž�����Ұս����32�����ɹ�ɳ���ӣ�����ֱָ�ࣨ��������ī����һ���º���֧�����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᭣��Ҷ����еĵط����IJ��ӽ�ռ���ൺ���ҵļ��磬�Ӵ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͵�ս�ҡ�
�����Ӹ����ң���Ҳ������·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һ�����ӡ�����1943���һ��ս���и������ˣ�Ϲ��һֻ�۾����Ӵ����۹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IJ���®�����ҵ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ⳡս����
����һ����ҹ��һ֧����С�ֶ��ڻ���һλ���ľ�����Ҫ������˽�����·�أ�����ɳ����ʱ���ӱ����ݵ���Ĺ��ӷ��֡������ȷ���һ����ǹ��Ȼ���ɳ������һ·ɱ��ɳ�������ϵĺ����֡�
����һƬĹ�أ���ľ���죬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ߺ����У�����˸��ɳ����600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Ƕ��������
С�ֶӹ���ʱ����ǹ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ʣ�µı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й϶���ƵĿ�ɱ�������ӵ������죬�ֵ��ֺݡ���һ�ù��ɱߣ�һ��������Բ������һ���ӰѶӳ���ͷ�������룬�ӳ�����һ���ˤ���ڵ��ϣ��������Ƶġ��¹��º��װ��Խ�������һ�ء���ǹ�ִ���һ���۰�б�ſ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һֻ�ִ��һ���ӵ���ֱ��ͷ����һ������һ�����ɣ�ǹ����ͣ��ͨѶԱС���ʮ���꣬��С��������ӣ���һ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أ����۾��ֵؿ����Լ����°������˵��ڵأ��ϰ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¡�
����˱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û��һ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塣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һ����һֻ�۱������Ϲ�����ӱ��������Һõ���һ���ؿ�ˮ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ת��תȥ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˼�ǹ���뿪�������ӽ��ҵ���һ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ӵ�һ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ͷ������ȥ������Ź��ӵ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Ķ��Ӻʹ��Ȱ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ӵ��ں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̵ij��Ӷ����˳�����
Ѫ��ģ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˾Ȼؼң��ε����ѣ�����ȱҽ��ҩ��û�еõ���ʱҽ�Σ�����º�ȥ���ˡ�����ǰ�������ѵ���˵�����õ��ģ��������Ǹ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ᣬ���ǻ��к����ӹ���
��ڲ�����ѧ����һ�衪�����Ž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ϲ���Ǹ�ʵ�������䣺
���ŷ���˹�ٿ���
��һ�в��������ƶ�������
����̫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ɣ��������й���
�������ɹ�â��
�����ʱ���߸����ź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Ǵ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ɡ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ģ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
������ͺ������Ӳ����ź��ض���˵�������ô��ʵ��һ���ˣ����ﻹ�н������ӣ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ʲô��·ѽ��
�ҷ��ʣ�����Ϊʲô����·�أ�
�����ӵ���һֻ���ۣ�����¶����һ����ָͷָָ�죬��ָָ�أ�ŭ�����
���Ӳ�һ�����ҼҸ��ձ����Ӳ������죡�뵱���ҵ��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ൺ��2��ɴ����24�����̣�8�䵱�̣�3�����š����С����ͷ�ϵĴ�С�ֿⶼ�����Ǽҵġ��Ҹ���һ��С檸����ӵķ���ٹ���ɼ飬�����¶�����Ƿ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Ҽ���Ϸ�����ը�����ձ��˽��ƾͼƣ�ץ���Ҽ���ʮ����ˣ�ֻ�����Ҹ��ף�������Ǯ���ˡ����˵�Ա��ǧ������һ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ҽ�㡢���ã�ÿ��һ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Ҫ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Ǽҵļҵף�������ۣ������ǼҵIJ�ҵͳͳ��ռ��ȥ�Ű��ݡ����ҳ��˼������ϵ�Ҳ�����ˣ��Ҳ�Ҳ���ˡ����ӵ�ȻҪͶ��·������ѩ�ޣ������Ӹɵ���ѽ��
���Ҹ���˵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Բ��顣�����Ӽ���Ȼ�Ǵ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Ǻ�����죬���ձ���ѧ�����Ͳμ�����ë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ǰ�����ˡ������Ҳ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Ӽҳ�����ɳ�����IJ���ȫ����ҵ�����ൺ���ձ�������һ�ա���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ൺ�⸴֮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Ľ��մ�Ա��æ���Լ����ƣ�û����Ϊ���ֲƲ���
��ź������ӵ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ݣ�û�����磬Ҳ��ȥ�����Ӹɻ�����Բ�®��Ѳ�κӵ̣�è��Ϊ�飬���Ϊ�ڡ��������Ǵ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ˡ�
�����dz����ܵ�����ӵ����IJ�®�����˵���Ǵ�ľ��¡�
��ʱ�������ӻ������ϵ���裬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룬����ӳ��Ұ�����µĻ�ԭ�е���ʷ��
������Ҳ�������ںӵ��ϣ����Ŵ����ˮ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¡�ӭ����ϼ���ͱ���ϼ��
2023��8��24��
ʮ�������꣬���߳��¶�ͯ�꣬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ꡣ����1976�꣬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ȥ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ӵ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ź�ɴ�������۾����ܿ��������ߣ����Ӷ�һ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ֵĴ��ֱ������͡�������Щ���ֱ������˵ڶ��������ӣ������Ǵ�ǹ�ĵ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ĸɲ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Ů�ģ���֣��С��ס���Ҽҡ�
���ã���ĸ������ס���ļ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ʯ�꣬��ʯ������䣬�����ļ¡�ʪ�ȵ�7�³�������¶������ίԱ��Ҳ���ˣ���һ�Σ��ҷ�����֣��С����Ҳ�����˺�ɴ��
��������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ѣ��ض�ɽҡ��ĸ��˵��������Ҫ���˰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һ�Բ�������֣��С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ɫ���š���Щ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Լ������IJ�������ſ��ᣬ�����Ǵ�ġ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Ʋ��ܲ��ʣ����˺������ơ�
9��9�����磬�����ӽ���֪ͨ������Աֹͣ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Ҫ�㲥��������ʱ������С����һ����̫����Щ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ڿ��С����ߵ�����ͻȻ�Գ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ǡ�����Ĵ����ȿ�ʼ�Ű��֣����˺��Ӷ��ֵ�һ����ɴ�����ڸ첲�ϡ��������Ķ�ĸ��˵�������˼����ˣ��ܺú����ǵ���ͣ���Ҫ��˵������
��Ȼ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ſ�ʼ���Ÿ��棬ȫ���˶���ɥ��������һ�ţ�����һ����ͥ�������õĻ�С��͵�Ż�Ц֮�⡣
�ڶ��죬ѧУ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ã���ʦ������һ����ƻ�������Ҵ���ȫ��ͬѧ���ԡ����Ե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ˣ�ӡ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Ǹ���ƻ��������
��̫�����䣬���dz��˱�ʹ����Ҫ�ǿ־壬��Ҷ���֪�����Ժ�����ӻ���ô����ȥ��
ס�ںӵ��ϵġ������ӡ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·��Ѿ����˼�ʮ���ˣ��ܲ�����һ���˶�����ȥ���ɡ�û�¶����óԳԣ���˯˯��
�������ӡ��Ļ������ľ�������ȴ�ܿ�Ӧ�顣����һ���£������ֻ���ϲ�ؿ���ᣬ����Сѧ��Ҳ���Ŷ�������ȥ���У���ף������ץ�������š�
��ף��Ὺ��û���죬����̨�ġ�Ӣ�����䡱�������Ļ��������ʤ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ڶ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Ҳ��Ȼ�����ˡ�
������ף��������˳��У�ѧУ��ʼץѧϰ����һ��ȫ�꼶ͨ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ǰé�������һ֧�ֱʺ������ʼDZ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IJ����ϣ���ĸ�ܸ��ˣ���Ҳ���Ժ���
��㺬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ң��ĵܣ���Ҫ�úö��飬���ϸ��У�
�������ʱ�������п���Ӹɲ��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Ӷ�����Ȩ������ܿ���һҲû���ɸ��У������Ҳһ����
���и�ͬѧ�С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IJ����ǿ顰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Ҷ�ʱ�������յ�˵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̫���ˣ�ʮ���˲���һ�������ǻ������˰ɡ���
��ʵ���Ǹ��ܴ�����ѧ����һ�ʷ�����д��Ư�����ˡ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Ǵ�Ψһ�����ൺ��У�ģ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ൺ��Ӫ��ó��˾�ĸɲ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ȻҪ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С���ʱ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룬ʮ����һ����ʲô�ѵģ�
��ʦ˵����־�����Զ��������ҿ�����ƽ�ȶ��У�����᭶��顣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Ŭ�������ż״��һ������ѧ��ľ��������ͨ���ж�û��ȡ�����ǵ������Ӵ˷ֲ档
���ǰ�����ɼ��������ͬѧ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˸��У��������е�Ҳû�п��ϴ�ѧ������Ϊ�и���ѧ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ͨ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ʦת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У���е�������ͨ����ѧ�õ���ѧ��ƾ�����ոı���ũ�����ݡ�
�ҳ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е�־����Ŭ�����꣬������Ӧ��û�����⣬����ȴ��һ��֮���Զ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ʳ��ũ��
��
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½��ġ����ѡ���һ���ļ���һ������ÿ�������ɫ�ij��ۣ���һ������ɫ����ձñ��һֻ�����ۣ���һֻϹ�ˣ����ϻ�����һ������ĵ��ۡ�������һ�ѻ���ɽ����ӣ�����ȥ���ϰ�ʮ�ˣ���˭Ҳ��֪��������ʵ���䡣������һ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һֻ����˯������ɫè����ֻ�µ���«������ס�ڴ���ӵ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ϴ��һ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Ǹ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IJ���®��
��˵�����Dz�����ӵ��ǧĶ����и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˵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ɶ�ã�����ȡ�����̡�
�����ڸ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ʱ���ڵ����ϼ������ģ��������Ϲ���һ������һ���ȵ��ϻ��۾��������۾���ϸ��������һ�������һ����צ�Ƶ���ָ�����ҵĶ�ͷ��˵������ҵ��Ĺ��ӣ�ü�ۣ���ͣ��ر��DZ�ͦ�ı��ӣ��е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ӡ�
����Ҳ���Ǹ����꣬�����ҸϽ����ߣ����߱�˵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ǻ��ˡ��IJ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ҵģ�
�ؼ���ĸ�ף���ӵ��ϵ�һ������ͷ˵�Ҹ���ү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ô����û������ү��
ĸ��ͣ������Ļ�ƣ���Ȧ���ˡ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ȥ��
����ס�ں�֣��IJ����ϵ�С������Ҳ��ǵ��Dz����ʹ������ˣ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֪����ĸ��С��ʱ����ү��ȥ���ˡ����Ǹ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ү�μ���һ֧�����λ��ӣ��ں����ֱ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ˡ��ӻؼҺ����˰���¾����ˡ�Ʋ����һ����ʮ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Ӻ��������ӡ����ѳ�˵������ү����ʱ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꣬��������꣬��С�˻����һ�����̡�
������ҵļ�ͥ���磬һֱӰ�쵽�ҡ��μӹ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й�һ��������飬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顣ĸ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ң��������û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û�˵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Ҳȱ��������
ĸ�Ļ��������᳤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ѵ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д��
��
�������һ���ϱ���ĺ�������Ҫ����ƽ�ȵ���һ�Σ����˸��䣬������ֱ�DZ�Ϊ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ɳ���壬�ָֻ����ϱ��ƺ����£�ע�뽺���塣
��ζ�������ĺ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˳�Ϊɳ���ӡ��ܶ���ǰ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Ͱ���ʯ�ţ���ɳ���š�����Ѵ�ڣ���ˮ���ۣ�ʯ�ű���û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ˣ�����ˮ���ӡ�
�������ӡ��ںӵ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ʱ��ͻȻָ��Сʯ�����ң���֪��������˾����
��ҡͷ��һʱû��Ӧ������
����˵���Ͻ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º��г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һƥ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֧����ǹ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ʮ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ſ���ǹ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ʹ�����С���Ϲ��ӡ����ൺ���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簡��
��ͻȻ��������˵����˾��Ĵ�����¡�������Ц������֪��������˾�˫�ִ�ǹ��˭���Ų������棬������˦�־���һǹ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ء�
������Ц�ˣ�����Ϲ��ġ���˾����书���ܺȾ�����ġ��������Ҳ����ġ���˵ֻ�������Դ�ǹȥ��ë��ϯ��
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ϲ���˵����˾��Ĵ��棺��˾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ݺὺ��ʮ���꣬�Ž��������Ԫ�����质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24��˾�����һ����ȫ���ˡ��Ա�ԭ����ᰡ���Ͻ�����ί�ε��ݱ�12ʦ�н�ʦ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ü����̾ὺ��ʮ���꣬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ˡ��Դ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ͷ�����¡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ͷ������٣��������վ��н��и��ָߵ��������ձ�ί���˸���У�ų���Ҳ�ڽ��ر���§�ݴ����ӣ����ˡ�����ϵ�ʱ���ϼ�������һ���¡��������˰��죬������ϸ�������ҫ�䡣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ͣ�ȴ�ǵ��ϼ������ˡ������ϼ���˭��ս����ԣ��������Ұս��˾�����
������ü��ɫ�裬˵�����ս�ۣ���ĭ��ɣ���ԣ�ָ���14���ˣ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Χ�ż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Լ�����ʮ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ڰ�·�ϴ�Ԯ��һ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Ȫ���ư�躣�˭֪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Ӽ�ѽ������ʹ����˼��ϣ��ŵ�����Ȫ�ư�躸Ͻ����˻�ȥ����ս����ԣʮ�����˴���һ����硣��˾��һ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ȥ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ս�ۣ��ɽ�ս�ۣ�������ս��ͳͳû���ķݡ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ѽ�������˲�ȥҽԺ�������ϱ��ӵ����˸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ָͷ���ӵ��۳������˿�Ĩ�ϵع��ͣ�û������ˡ�
��ʵ�����ί�п���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˺ü����ݶӣ������ھ���һ�ߣ�������ʦ�����Ĵ���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ൺ����·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ڳ��ʲ������һ����
�����ڹ��һ��������һ��ѵ���¾����Ѽ�֧�������ӡ��ط���װ��ѵ�������齨�ɵ�32��������֧���ӣ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ൺ��
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ʷר�ң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ѽ���û�μӻ������ɽ�ս�۵�������
��
վ�ڴ������ͷ���ҵ���ǰ�������ֳ�����һ�����棺
һ֧�����н���ʢ����ơ�ƻ���ԭҰ�ϣ��峿�ķ������ɢ���ŵ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һֱ���쵽��ʡ�ɳ�����Զ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ʿ���ǵ���ǰ�������ʣ���ʧ�����ɫ��Ũ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ĵ̰��ϣ�Ұ���ͷס���չ���һ�ֲ��£���ϡ�м�����͵��¹⣬�����Ƶ�϶�����佫������һ������죬�ڳ�����ӭ��������չ��Ѫս֮���ɳ���ϣ�ս���ݺᣬ���м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ʬ�壬�������˵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Ѫ��ζ�������εΣ������賿�����⡣
ɳ�����ϵ�Сʯ���ѱ�ը�ɼ��Σ��������˵����ں�ˮ�սʿ�Dz��ò����ɹ��ӡ�����ӳ�ں����ϣ��������ԣ�ˮ����ֻ�Գ�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ǧ����ƥ��������̤̤��������ˮ�����ӵ��W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أ��������У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
����1949�����£��й������ž�����Ұս����32�����ɹ�ɳ���ӣ�����ֱָ�ࣨ��������ī����һ���º���֧�����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᭣��Ҷ����еĵط����IJ��ӽ�ռ���ൺ���ҵļ��磬�Ӵ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͵�ս�ҡ�
�����Ӹ����ң���Ҳ������·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һ�����ӡ�����1943���һ��ս���и������ˣ�Ϲ��һֻ�۾����Ӵ����۹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IJ���®�����ҵ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ⳡս����
����һ����ҹ��һ֧����С�ֶ��ڻ���һλ���ľ�����Ҫ������˽�����·�أ�����ɳ����ʱ���ӱ����ݵ���Ĺ��ӷ��֡������ȷ���һ����ǹ��Ȼ���ɳ������һ·ɱ��ɳ�������ϵĺ����֡�
����һƬĹ�أ���ľ���죬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ߺ����У�����˸��ɳ����600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Ƕ��������
С�ֶӹ���ʱ����ǹ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ʣ�µı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й϶���ƵĿ�ɱ�������ӵ������죬�ֵ��ֺݡ���һ�ù��ɱߣ�һ��������Բ������һ���ӰѶӳ���ͷ�������룬�ӳ�����һ���ˤ���ڵ��ϣ��������Ƶġ��¹��º��װ��Խ�������һ�ء���ǹ�ִ���һ���۰�б�ſ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һֻ�ִ��һ���ӵ���ֱ��ͷ����һ������һ�����ɣ�ǹ����ͣ��ͨѶԱС���ʮ���꣬��С��������ӣ���һ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أ����۾��ֵؿ����Լ����°������˵��ڵأ��ϰ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¡�
����˱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û��һ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塣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һ����һֻ�۱������Ϲ�����ӱ��������Һõ���һ���ؿ�ˮ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ת��תȥ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˼�ǹ���뿪�������ӽ��ҵ���һ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ӵ�һ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ͷ������ȥ������Ź��ӵ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Ķ��Ӻʹ��Ȱ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ӵ��ں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̵ij��Ӷ����˳�����
Ѫ��ģ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˾Ȼؼң��ε����ѣ�����ȱҽ��ҩ��û�еõ���ʱҽ�Σ�����º�ȥ���ˡ�����ǰ�������ѵ���˵�����õ��ģ��������Ǹ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ᣬ���ǻ��к����ӹ���
��ڲ�����ѧ����һ�衪�����Ž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ϲ���Ǹ�ʵ�������䣺
���ŷ���˹�ٿ���
��һ�в��������ƶ�������
����̫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ɣ��������й���
�������ɹ�â��
�����ʱ���߸����ź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Ǵ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ɡ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ģ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
������ͺ������Ӳ����ź��ض���˵�������ô��ʵ��һ���ˣ����ﻹ�н������ӣ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ʲô��·ѽ��
�ҷ��ʣ�����Ϊʲô����·�أ�
�����ӵ���һֻ���ۣ�����¶����һ����ָͷָָ�죬��ָָ�أ�ŭ�����
���Ӳ�һ�����ҼҸ��ձ����Ӳ������죡�뵱���ҵ��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ൺ��2��ɴ����24�����̣�8�䵱�̣�3�����š����С����ͷ�ϵĴ�С�ֿⶼ�����Ǽҵġ��Ҹ���һ��С檸����ӵķ���ٹ���ɼ飬�����¶�����Ƿ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Ҽ���Ϸ�����ը�����ձ��˽��ƾͼƣ�ץ���Ҽ���ʮ����ˣ�ֻ�����Ҹ��ף�������Ǯ���ˡ����˵�Ա��ǧ������һ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ҽ�㡢���ã�ÿ��һ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Ҫ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Ǽҵļҵף�������ۣ������ǼҵIJ�ҵͳͳ��ռ��ȥ�Ű��ݡ����ҳ��˼������ϵ�Ҳ�����ˣ��Ҳ�Ҳ���ˡ����ӵ�ȻҪͶ��·������ѩ�ޣ������Ӹɵ���ѽ��
���Ҹ���˵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Բ��顣�����Ӽ���Ȼ�Ǵ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Ǻ�����죬���ձ���ѧ�����Ͳμ�����ë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ǰ�����ˡ������Ҳ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Ӽҳ�����ɳ�����IJ���ȫ����ҵ�����ൺ���ձ�������һ�ա���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ൺ�⸴֮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Ľ��մ�Ա��æ���Լ����ƣ�û����Ϊ���ֲƲ���
��ź������ӵ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ݣ�û�����磬Ҳ��ȥ�����Ӹɻ�����Բ�®��Ѳ�κӵ̣�è��Ϊ�飬���Ϊ�ڡ��������Ǵ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ˡ�
�����dz����ܵ�����ӵ����IJ�®�����˵���Ǵ�ľ��¡�
��ʱ�������ӻ������ϵ���裬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룬����ӳ��Ұ�����µĻ�ԭ�е���ʷ��
������Ҳ�������ںӵ��ϣ����Ŵ����ˮ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¡�ӭ����ϼ���ͱ���ϼ��
2023��8��24��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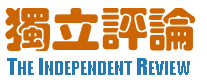


 [����]
[����] 