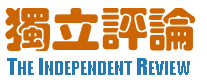һ���˵ĸ����ʽ
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Ǹ��H����ֱ��Ϧ���б����߀��֪�����N�k����Ȼ�����ʮ��ǰ�ڰˌ�ɽ�Տd����һĻ���ҲŽK��ҵ����츸�H�ķ�ʽ��2003�괺�һر��������ʣ�����Ҳ�]Ҋ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һ����ԒҪ�����f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K��֪����Ҫ�f����ʲ�N���ұ��ȸ����˷��_���H��e��Ȼ���Һͽ��ȡ���˸��H�Ĺǻң��҂��]�Ќ�����ڰˌ�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游�H�ܽ^����Ч��һ�����@�����࣬���䌍��֪���Dz����`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Ȼ�����鋌���BĹ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ʮ���꣬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ܸ��������_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һ����Q�࣬ȡ������Ĺ�V�e�ǻң����ְֵĹǻ�һ�����M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҂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ǡ�����]���ĺ���֮�g�������e�ˡ�����һ˲�g����Ҳ��e���P��Ї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l��һ�У��ҏصג������ҵ��Jͬ��������ʮ�Ěq���꣬���һ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ң����Xһ���pҲ���x���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ļ����Ձ�����@���x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ҁ����@�����ϣ��Žo�����Ǵ��ס����ݡ������ұ�����һ��Ҳ�]�ܔ[Ó�@�����ݣ�߀�ڴ�ǰ�װخ���ʮ���걻�������ͨ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ߡ��@�������ҵ�������츸�H�ķ�ʽ���Һ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ģ��������ǰ�o�O�ӌ��ţ�����Ҫ����ĸ�ĸ��������һλ�����ߵ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
2003�����³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סլ���ڴ��ɲݳ���һ������ʼ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ҵ����䣬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˱�ɫ���ܵ�����˵�ְ����ʱ��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ΰ����ڣ�Ҫ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ǩ֤�ع�������̸�����ף�ǡ���յ���ѧ���д��٣�������үү���ˣ�������˵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ǩ֤�ع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Ӵ�ȥ�궬��������Ȼ���죬���˴��ˡ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İ�������ƾ�ҵĻع����ţ�û��һ�����顣��ֻҪ�����ң����ĺ��Ƕ����ԡ�
�յ��ɵ������ͷ����ʼ������ҽ�������үү��һ�ۣ�����һ����үү�ݵ�������Ƥ�����ƣ��������˺����ѣ���̬��Ȼ��������˵Ц������Թ�ù�̫��߶������ù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ҽԺ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Ҳ��ͨ�ܵ����ڲ������ֻ������ְ�˵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Ҫ�������ƣ����һ�ȥ�����á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Ҵ�δ������غ�һ���˵Ĵ�Σ���ָ�������֮ң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У������²����Ƿ���ʶ���Լ�����Σ֮�������й��˵�ϰ�ߣ������ڲ��˸�ǰ���Բ����Ǹ��������֡����Լ�����ȴ�Ѳ���һ��Ī���ľ�־壬�·��Ǹ��ְ�һ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¿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ʡ�
�����й����صĽ�ֹ�뾳�����ϡ��ܵ����Ǿ���ͨ�������ʾ��������ү�ӱ������Ҫ����û��������ء��ܵ�ֻ�ò���һ���ţ��õ�����ǰ����ְ�����˵������ϣ����һ�����ں���ij��ӡ��������ڽ���ֱ֢��֪ͨ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ǩ���Ժ�һ����ݾ����ˡ���ǩ��һ���Լ��ľ����顣��3��22������4��40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3��2������췢�ָΰ��ģ�һ���Ŷ�ʮ���ģ��й�פŦԼ�����¹�ǩ֤��3��28�ղ�֪ͨ�ң�ǩ֤������ʱ�Ҳ�����ܵ�һ��ʼ��˵�������ְ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㡣�������ҵ�������ǣ��������ǹ�����һ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ϣ��Ҳſ��˳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ڵ绰�ϳ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˵�����ְ�һ����û�ܣ��ߵúܰ��꣬�Ǵ����ˡ�������һֻ��һֱ���գ��Ҹ����϶��ϲ��ϣ�������Ϊû�����㡣��
��Я��������29�շɵֱ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ƿ������ϵĸ���һ�ԵȺ��������һ�����ң��Գ��DZ����й����ֵ������ˣ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ý�塢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ۡ����Ӵ��������Ȼ��ͷ����ˡ���Ȼ��Ҳ��һ�����裬�����DZ�ɥ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飿
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ʽ��һ���Һ͵ܵܵ���ˮ̶ҽԺ̫ƽ�䣬�ӱ�����̧���ְ֡��������屻����һ����ɫ�ķ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ǹݵ��鳵���ˡ������ʽ����ŵ���ڰ˱�ɽ���ǹݡ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С��ְֵġ���֯�ϡ�������Լ̸��һ�Σ�˵��ʽ�е�����ʿҪ��������˼Ҳ�������ҡ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ұ���رܡ���ʽ����Ϊ���ν��У�ǰһ���ǡ��ٷ��ġ����Ҳ����ڳ������ǰ���֮��ר�����¼����ӵ���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Ϊ��һ�˾��С����ǵڶ������裬���Ҿܾ�����ֻ�����ڸ���˽�����ݵ���һ�棬��ʵҲ�á�һ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Ƕ����ˡ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ø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Ͼ��Ǵ��ϱ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ң��ҵܵܰ����ƹ�ȥ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ֳ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ҵ�λ���ϣ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κ������֣���ʾ���顣�º�ϸ�룬�ø��������ҵ�λ�ã�Ҳ���ǵܵ���ȡ���ġ�
��һ���˱����ڡ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档�������ܵ�Զһ�㣬���ڵ�����һ����ʯ̨�������ں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ԡ��ҼDz��ô�ǰ��û������ط������Ľ�����ȫģ�¹�͢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ߴ����ܣ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ʾ���ʧ�ޣ���ש���ơ������Ժ���ƴ����Ѱ�ְֵ���Ӱ�����ֵľ������Ҹ����ڻ���ƽԭ�Ķ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﹡�������ߣ�����һ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紺���ְ�һ�Ŷ��������ˣ����겻����ʮ���꣬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ʱ����ʹ����ꡣ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Ǹ��糿����ӡ��������ǣ���һ����˥���ˡ��ձ��ˡ����ˡ��������ʮһ�꣬��Ȼ����ȥ�����ڸ�У�ﱻ��ɡ���ͳ���İְ֡�����ʱ�־�����·��ʯ��ׯ���Ҿ������˳���ֻ֪��һ����ׯ�����֣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ij��������·�������ְֺܾ����ҵij��֣�����ס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ҵ���ͷһ�����ո˺��棬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̣�˳�ֻ��ݸ���һ֧���Ҵ�δ���ְ���ô�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˿������ѳ��͡����ϡ�����һЩʲô�����ǵ��ˡ������ְ����һس�վ����˵��˳�����ϴ���衣����ʮ�������ĸ���²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ͷʱ��ʮ���꣬��ʮ��Ŀ������Ժ���˳�ˣ�ֱ�������ʮ�꣬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ǵõ��˶�ʮ�����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ǵ������껪���Ǹ��糿�������У��ְֵ�������һ���⣬��Ҳû�е��࣬��Զ�����
�ְ������ĸȴ������˶��Ȼ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ƶȣ����й��������Ա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ڡ��ĸ�롸���ġ���ë��ˣ���Ҳ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һ�������ߡ���ʮ������й���ʼ���ã�ƶ�����ѣ��ְ�ȴ�ܵ���ί��ȥ�ィһ�������Ľ����о�������ר���о�������ٵ��͵��磬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ݡ��������ij��٣�ʹ�ְ��Ӷ�λ�Լ���һ�������Է�������ʱѡ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Ȼ���ʡ��������ܳ�ʱ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˼��֮������ң���ŷ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Ĵ���ʿ���й��Ŵ�Ҳ�������ϵķ��ͽ�����Ƕ�Ϊ���ǵ�����ܶ������˿���˵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ҵ�һ������ͬ��Щ����ʿ��ɮ������ȡ���Ҳ����ʷ�����е�һ�Ρ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ǰְ�д���Լ������ʣ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ǰд�ͣ���Ȼ�˿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ǡ��������ȥ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ʡ�
��Ȼ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ң�˵�ֵ����ˡ��ٷ���ʿ����ȥ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߽��ǡ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̧�ۿ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ϸ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ա��Һ������ȥ������ͷ��������İ�������ӵķ�Χ�У��Ҿ�����ȥ�����ҿ��Ʋ�ס�س�����ժ���۾�����ˮ���ɵ�ϣ���һ�����ڹ�ľ�еĸ��ס�����̬���꣬û��ʹ���һ˿�ۼ����ܿ죬���ǹ���Ա�������߸�������ȥ���Һͽ����͵����Ÿ�ǰ���˼ҹ����ţ��һ��ڷ��ų�ҭ������
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Ǹ��H����ֱ��Ϧ���б����߀��֪�����N�k����Ȼ�����ʮ��ǰ�ڰˌ�ɽ�Տd����һĻ���ҲŽK��ҵ����츸�H�ķ�ʽ��2003�괺�һر��������ʣ�����Ҳ�]Ҋ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һ����ԒҪ�����f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K��֪����Ҫ�f����ʲ�N���ұ��ȸ����˷��_���H��e��Ȼ���Һͽ��ȡ���˸��H�Ĺǻң��҂��]�Ќ�����ڰˌ�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游�H�ܽ^����Ч��һ�����@�����࣬���䌍��֪���Dz����`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Ȼ�����鋌���BĹ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ʮ���꣬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ܸ��������_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һ����Q�࣬ȡ������Ĺ�V�e�ǻң����ְֵĹǻ�һ�����M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҂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ǡ�����]���ĺ���֮�g�������e�ˡ�����һ˲�g����Ҳ��e���P��Ї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l��һ�У��ҏصג������ҵ��Jͬ��������ʮ�Ěq���꣬���һ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ң����Xһ���pҲ���x���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ļ����Ձ�����@���x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ҁ����@�����ϣ��Žo�����Ǵ��ס����ݡ������ұ�����һ��Ҳ�]�ܔ[Ó�@�����ݣ�߀�ڴ�ǰ�װخ���ʮ���걻�������ͨ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ߡ��@�������ҵ�������츸�H�ķ�ʽ���Һ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ģ��������ǰ�o�O�ӌ��ţ�����Ҫ����ĸ�ĸ��������һλ�����ߵ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
2003�����³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סլ���ڴ��ɲݳ���һ������ʼ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ҵ����䣬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˱�ɫ���ܵ�����˵�ְ����ʱ��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ΰ����ڣ�Ҫ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ǩ֤�ع�������̸�����ף�ǡ���յ���ѧ���д��٣�������үү���ˣ�������˵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ǩ֤�ع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Ӵ�ȥ�궬��������Ȼ���죬���˴��ˡ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İ�������ƾ�ҵĻع����ţ�û��һ�����顣��ֻҪ�����ң����ĺ��Ƕ����ԡ�
�յ��ɵ������ͷ����ʼ������ҽ�������үү��һ�ۣ�����һ����үү�ݵ�������Ƥ�����ƣ��������˺����ѣ���̬��Ȼ��������˵Ц������Թ�ù�̫��߶������ù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ҽԺ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Ҳ��ͨ�ܵ����ڲ������ֻ������ְ�˵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Ҫ�������ƣ����һ�ȥ�����á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Ҵ�δ������غ�һ���˵Ĵ�Σ���ָ�������֮ң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У������²����Ƿ���ʶ���Լ�����Σ֮�������й��˵�ϰ�ߣ������ڲ��˸�ǰ���Բ����Ǹ��������֡����Լ�����ȴ�Ѳ���һ��Ī���ľ�־壬�·��Ǹ��ְ�һ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¿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ʡ�
�����й����صĽ�ֹ�뾳�����ϡ��ܵ����Ǿ���ͨ�������ʾ��������ү�ӱ������Ҫ����û��������ء��ܵ�ֻ�ò���һ���ţ��õ�����ǰ����ְ�����˵������ϣ����һ�����ں���ij��ӡ��������ڽ���ֱ֢��֪ͨ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ǩ���Ժ�һ����ݾ����ˡ���ǩ��һ���Լ��ľ����顣��3��22������4��40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3��2������췢�ָΰ��ģ�һ���Ŷ�ʮ���ģ��й�פŦԼ�����¹�ǩ֤��3��28�ղ�֪ͨ�ң�ǩ֤������ʱ�Ҳ�����ܵ�һ��ʼ��˵�������ְ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㡣�������ҵ�������ǣ��������ǹ�����һ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ϣ��Ҳſ��˳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ڵ绰�ϳ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˵�����ְ�һ����û�ܣ��ߵúܰ��꣬�Ǵ����ˡ�������һֻ��һֱ���գ��Ҹ����϶��ϲ��ϣ�������Ϊû�����㡣��
��Я��������29�շɵֱ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ƿ������ϵĸ���һ�ԵȺ��������һ�����ң��Գ��DZ����й����ֵ������ˣ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ý�塢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ۡ����Ӵ��������Ȼ��ͷ����ˡ���Ȼ��Ҳ��һ�����裬�����DZ�ɥ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飿
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ʽ��һ���Һ͵ܵܵ���ˮ̶ҽԺ̫ƽ�䣬�ӱ�����̧���ְ֡��������屻����һ����ɫ�ķ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ǹݵ��鳵���ˡ������ʽ����ŵ���ڰ˱�ɽ���ǹݡ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С��ְֵġ���֯�ϡ�������Լ̸��һ�Σ�˵��ʽ�е�����ʿҪ��������˼Ҳ�������ҡ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ұ���رܡ���ʽ����Ϊ���ν��У�ǰһ���ǡ��ٷ��ġ����Ҳ����ڳ������ǰ���֮��ר�����¼����ӵ���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Ϊ��һ�˾��С����ǵڶ������裬���Ҿܾ�����ֻ�����ڸ���˽�����ݵ���һ�棬��ʵҲ�á�һ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Ƕ����ˡ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ø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Ͼ��Ǵ��ϱ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ң��ҵܵܰ����ƹ�ȥ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ֳ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ҵ�λ���ϣ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κ������֣���ʾ���顣�º�ϸ�룬�ø��������ҵ�λ�ã�Ҳ���ǵܵ���ȡ���ġ�
��һ���˱����ڡ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档�������ܵ�Զһ�㣬���ڵ�����һ����ʯ̨�������ں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ԡ��ҼDz��ô�ǰ��û������ط������Ľ�����ȫģ�¹�͢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ߴ����ܣ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ʾ���ʧ�ޣ���ש���ơ������Ժ���ƴ����Ѱ�ְֵ���Ӱ�����ֵľ������Ҹ����ڻ���ƽԭ�Ķ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﹡�������ߣ�����һ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紺���ְ�һ�Ŷ��������ˣ����겻����ʮ���꣬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ʱ����ʹ����ꡣ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Ǹ��糿����ӡ��������ǣ���һ����˥���ˡ��ձ��ˡ����ˡ��������ʮһ�꣬��Ȼ����ȥ�����ڸ�У�ﱻ��ɡ���ͳ���İְ֡�����ʱ�־�����·��ʯ��ׯ���Ҿ������˳���ֻ֪��һ����ׯ�����֣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ij��������·�������ְֺܾ����ҵij��֣�����ס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ҵ���ͷһ�����ո˺��棬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̣�˳�ֻ��ݸ���һ֧���Ҵ�δ���ְ���ô�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˿������ѳ��͡����ϡ�����һЩʲô�����ǵ��ˡ������ְ����һس�վ����˵��˳�����ϴ���衣����ʮ�������ĸ���²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ͷʱ��ʮ���꣬��ʮ��Ŀ������Ժ���˳�ˣ�ֱ�������ʮ�꣬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ǵõ��˶�ʮ�����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ǵ������껪���Ǹ��糿�������У��ְֵ�������һ���⣬��Ҳû�е��࣬��Զ�����
�ְ������ĸȴ������˶��Ȼ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ƶȣ����й��������Ա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ڡ��ĸ�롸���ġ���ë��ˣ���Ҳ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һ�������ߡ���ʮ������й���ʼ���ã�ƶ�����ѣ��ְ�ȴ�ܵ���ί��ȥ�ィһ�������Ľ����о�������ר���о�������ٵ��͵��磬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ݡ��������ij��٣�ʹ�ְ��Ӷ�λ�Լ���һ�������Է�������ʱѡ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Ȼ���ʡ��������ܳ�ʱ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˼��֮������ң���ŷ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Ĵ���ʿ���й��Ŵ�Ҳ�������ϵķ��ͽ�����Ƕ�Ϊ���ǵ�����ܶ������˿���˵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ҵ�һ������ͬ��Щ����ʿ��ɮ������ȡ���Ҳ����ʷ�����е�һ�Ρ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ǰְ�д���Լ������ʣ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ǰд�ͣ���Ȼ�˿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ǡ��������ȥ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ʡ�
��Ȼ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ң�˵�ֵ����ˡ��ٷ���ʿ����ȥ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߽��ǡ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̧�ۿ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ϸ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ա��Һ������ȥ������ͷ��������İ�������ӵķ�Χ�У��Ҿ�����ȥ�����ҿ��Ʋ�ס�س�����ժ���۾�����ˮ���ɵ�ϣ���һ�����ڹ�ľ�еĸ��ס�����̬���꣬û��ʹ���һ˿�ۼ����ܿ죬���ǹ���Ա�������߸�������ȥ���Һͽ����͵����Ÿ�ǰ���˼ҹ����ţ��һ��ڷ��ų�ҭ������